(翻攝自電影《霸王別姬》)
《霸王別姬》上映於1993,由陳凱歌導演,張豐毅、鞏俐主演,獲得第46屆法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,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獲得這個獎項的華語電影。並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百大不朽電影之一。這部閃耀不朽的電影儘管在國外先後獲得三十八項大獎,卻因為牽涉文革歷史,難以在中國上映,更不用說獲獎。這對被外媒評為「中國最偉大的電影」的《霸王別姬》顯得格外的諷刺。
初次與《霸王別姬》見面是在編劇課堂上,老師要我們看三部電影作為課堂的教材,分別為李安的《臥虎藏龍》,馬克福斯特執導的《口白人生》,蔡明亮的《河流》。課堂裡有同學問老師,為什麼不選擇《霸王別姬》來當作課前教材而選了《臥虎藏龍》,老師當時答道由於武俠屬於東方世界的特有文化,相當於西方奇幻,無論時間如何推進這都是屬於東方世界明亮的特色之一。
難道京劇不是東方世界的特有文化嗎?
當然不是這個意思。京劇當然是東方世界的特有文化,而且有著悠遠的歷史。不過,與其說《霸王別姬》是形式上的京劇故事,不如說是兩個戲子和整個中國的歷史故事,著重的是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(虞姬與菊仙)的心靈,在那個起伏顛簸的歷史上所展現深刻的、荒唐的、蕭索的、崩塌的文化。《霸王別姬》當然是一部了不起的電影,即使在27年後的現在,華人電影也還沒有一部電影會拿來與它比肩。
講遠了,為什麼選擇《臥虎藏龍》而不是《霸王別姬》呢?我想是因為《臥虎藏龍》是非常形式上地使用武俠元素演出,也就是說,用著武俠元素和劇情本身相依相傍,如果將武俠的元素去除後,《臥虎藏龍》就不是《臥虎藏龍》了。而《霸王別姬》雖然兩位主角即使今天他們不是京劇出生,而是別種文化藝術,只要編寫的夠好,那一樣行的通,因為在《霸王別姬》這部戲裡閃閃發亮的不是那身穿戲服的楚霸王與虞姬(形式上),而是那兩顆在塵世打滾受傷的靈魂。

※(以下全為劇情) - - - - -
「您二位有二十多年沒在一塊唱了吧?」
「二十一年了。」段小樓笑著搭訕。
「二十二年。」程蝶衣冷冷地說。
「對,是二十二年。我們哥倆也有十年沒見面了。」段小樓連忙說。
「十一年,是十一年!」
《霸王別姬》開場的短短幾句話彷彿演出了程蝶衣那自我、自戀、執著的性格。你不記得我們究竟分隔多久,我偏偏記得,你講錯了多久沒見面,我偏偏牢牢記住。從開場對白就已經細膩的拉起程蝶衣執著的一生。恰如他師父告訴他的從一而終,對戲劇、對角色、對愛情、對一個男人。對段小樓來說楚霸王只是戲裡的角色,但程蝶衣卻活活將自己演成了虞姬。
「我本是女嬌娥,不是男兒郎。」是《思凡》裡的一段自白,寫的是小尼姑色空,年紀輕輕就被送進了尼姑庵,學佛讀經的她,卻無法克制地想到了凡間的一切,包括愛情。提到戲曲,都知道女怕《思凡》,男怕《夜奔》。自幼被妓女母親送到京劇戲團練習的程蝶衣,因為長相清秀被選為旦角,練習到「我本是女嬌娥,又不是男兒郎。」唱詞時,卻彷彿抗拒著成為小尼姑色空,屢屢無法入戲,錯誤唸成「我本是男兒郎,又不是女嬌娥。」
「若要在人前顯貴,必得人後受罪。」他知道,所以刻苦練習是他的日常。唱不好,挨打。練習後,唱不好,仍然挨打。蘆葦森森,月光粼粼,刻骨的訓練彷彿月光拓在他們身上,他們終於逃出戲班子,在大街上短暫的獲得自由,儘管跑出戲班子,他們仍是跑到戲院,彷彿離不開戲。他們看著戲院裡戲子在人群的簇擁中走向舞台上,戲台上燈光輝煌,穿著華麗輝煌魁偉的楚霸王上陣,擊倒敵兵無數。胡琴、金拔、堂鼓鳴奏而起,楚霸王顯得無比高大。「他們是怎麼成角的,得挨多少打呀。」一個戲班子的學生說,一滴淚從程蝶衣臉上流了下來。
我本是男兒郎,不是女嬌娥。程蝶衣仍然無法獲得自己的認同,在一次給戲園經理表演時將戲詞說錯。眼看經理拂袖而去,師弟刻苦練習卻屢屢受挫,段小樓激動的將程蝶衣摔到椅子上,拿起菸斗插進程蝶衣的嘴裡一陣亂攪,一絲鮮血從程蝶衣嘴角滑落。我本是女嬌娥,又不是男兒郎。他終於說對了,卻也預示著今後人戲不分的一生。

「蝶衣,你可真是不瘋魔不成活呀!」
段小樓愛上了青樓裡的名妓菊仙。在他口中原是一個逢場作戲,不過只是演了一齣「武二郎與西門慶」段子罷了。哪料出身名妓的菊仙心裡也有一股傲氣,竟為了一句戲言替自己贖身。
當菊仙把在妓院裡多年積攥的珠寶、髮式一件一件地從她的人生中褪下來時,老鴇衝著她氣急敗壞地罵道:「還真想當太奶奶啦你?……我告訴你,那窯姊永遠是窯姊,你記住我這話,這就是你的命。」菊仙只是淡淡地回道「成,回見您啦。」

《霸王別姬》是一個時代裡,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的故事(或兩個男人與一個女人)。菊仙既潑辣又冷淡,細膩又極為勇敢,她從青樓一躍而下,奔向段小樓喝了訂親酒的婚約。菊仙的出現在蝶衣心上紮了一根刺,彷彿一次呼吸就會痛一次。程蝶衣愛上楚霸王,段小樓卻不愛虞姬。在人間,他們只是戲子罷了。當蝶衣看見菊仙時,就清楚地知道了,菊仙是女人,而虞姬卻是男人。
「聽說,你在八大胡同打出名來了。」程蝶衣道。
「這武二郎碰上西門慶,不打,不打能成嗎?」段小樓回道。
「這麼說,有個潘金蓮啦?」
「這是什麼話?」
「你想聽什麼話?」
「不過就是救人解難,玩玩唄,又不當真。蝶衣,什麼時後去逛一逛,就知道了。」說到這,段小樓搓著手,頗有種猥瑣的味道。
蝶衣拂袖而起,撞得妝台哐啷作響。
……
「…師父說的從一而終!師哥,我要讓你跟我,不對,我們就好好唱一輩子戲,不行嗎?」
「這不小半輩子都唱來了-」
「不行!說的是一輩子,少一年,一個月,一天,一個時辰,都不算一輩子!」
蝶衣,你可真是不瘋魔不成活呀!

「那起碼日本人是懂戲的!」日本人進城了,國民政府進城了,共產黨進城了。
日本軍官看戲是安靜的,他們在台下安靜地看,一直到精采處才站起來鼓掌,就像在《霸王別姬》裡一向鍾情藝術和戲劇的晚清貴族袁四爺。程蝶衣鍾情藝術,藝術是他的一生,他也不在乎底下看的人是誰,能夠明白藝術的觀眾就是他的觀眾。但是段小樓是有脾氣的,他的脾氣與日本人打交道,被日本人捉了去。為了換段小樓出來,程蝶衣上日本人那唱哩一齣戲。
國民政府看戲是起鬨的,他們調戲在戲台上的蝶衣,當作那是青樓女子。一齣戲,國粹,就像一場鬧劇。「戲園子沒有用手電筒晃人的規矩,連日本人也沒這麼鬧過。」段小樓無法坐視,與看戲的國民兵發生衝突,在衝突裡菊仙肚子的小孩沒了。國民軍把蝶衣抓去審判,因為他替日本人唱過戲。在段小樓與菊仙的哀求下,請出了鍾情藝術、戲曲,並在當時頗有名氣聲望的袁四爺出庭說話。
「方才檢察官聲言程之所唱為淫辭艷曲,實為大謬!程當晚所唱的是牡丹亭遊園一折,略有國學常識者都明白,此折乃國劇文化中之最精萃。何以在檢察官口中,竟成了淫辭艷曲了呢?如此糟賤戲劇國粹,到底是誰辱我民族精神?滅我國家尊嚴?」袁四爺在法庭上的一席話,彷彿替所有法庭裡學過戲劇的人都出一口氣。
蝶衣卻如此回答:「堂會我去了,我也恨日本人,可是他們沒有打我……如果青木活著,京劇就傳到日本國去了。」

國民兵走了,共產黨接手。他們輕易地槍決即使在國民政府前說話也有一席之地的袁四爺,彷彿在這條革命的路上無有阻礙,所有擋路的都會碾碎。這讓在面對日本兵、國民兵時還算有霸王氣概的段小樓怕了,真世界裡的四爺輕易地被槍決,而他只是在戲裡的假霸王罷了。在共產政府統治下,政治開始強制性的干預藝術,毛澤東推動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更批鬥舊文化,戲劇和京劇淪為舊傳統裡封建的思想,被批鬥為阻礙民族進步的石頭。
在那個人人批鬥,人人自危的社會裡,段小樓連忙將戲服、劇本燒了,生怕沾上封建與舊時代的邊。程蝶衣燒了自己的戲服,就像燒掉自己的(烏托邦)。然而社會卻沒有這麼容易放過他們,身為過去傳統藝術的一份子,仍然被拖出來,扣上反革命的罪名,按在大街上,人們起舞,喊著口號,歡天喜地。程蝶衣與段小樓被粗糙地畫上霸王與虞姬的妝容,臉上像是被煙燻過,黑一塊,紅一塊。大火在他們面前熊熊地燒,穿著解放服的人們高高在上。
至此,這場無情的鬥爭逼出人們的自私、醜陋與變態。蝶衣與小樓終於在群眾的逼迫下互相揭發。整座電影營造的戲劇之美,彷彿是一座著火的宮殿,在批鬥裡燃起熊熊的火光。

「他是戲癡,戲迷,戲瘋子!」段小樓說。「他是只管唱戲的,他不管底下坐的是什麼人,什麼階級,他都賣力地唱,玩命地唱。」
「你避重就輕,你不老實!」
「段小樓不投降,就教他滅亡!」批鬥群眾趕緊吶喊。
「抗日戰爭剛剛開始,他就給日本侵略者坐堂會,他就……他就當了漢奸!」他穿著霸王的戲服,被按在地上,心裡的霸王徹底死了。
「打倒程蝶衣!」有人呼喊。
「打倒程蝶衣!」群眾趕緊喊著口號。
「打倒程蝶衣!」段小樓連忙附和。
才子佳人,帝王將相,都是一切牛鬼蛇神。他們要互相揭露,互相批鬥,程蝶衣揭發段小樓取妓女為妻。解放人民連忙附和,要揭發更多。
「段小樓,她是不是妓女?是不是!」解放人民扯著段小樓的衣服問。
「你愛她嗎?愛不愛?」
「……不!不愛!不愛她!」
「真的?」
「不愛,真的不愛,我和她劃清界線!」
大火熊熊燃燒,隔著煙,菊仙看向段小樓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?
「我跟她劃清界線了!」段小樓大叫。
菊仙穿著那天與段小樓成親的嫁衣在家裡自縊了。
……
十一年後,段小樓與程蝶衣終於在體育館裡重逢。
只是段小樓仍是段小樓,虞姬仍是虞姬。從一而終是師傅在戲裡給他深深的告誡,那天四面楚歌,項羽讓烏騅馬離去,烏騅馬不去。讓虞姬離去,虞姬不肯。她抽起寶劍,對項羽作最後一次斟酒,最後一次舞劍,而後虞姬終於向她心裡的霸王自刎了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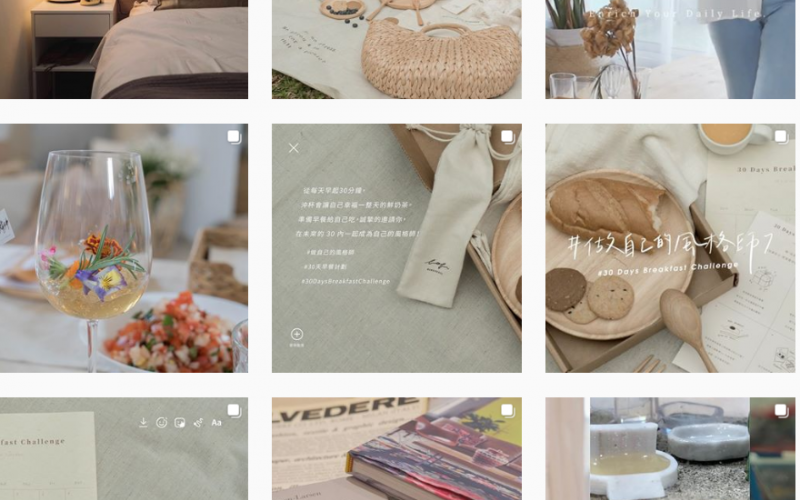





讀者回應